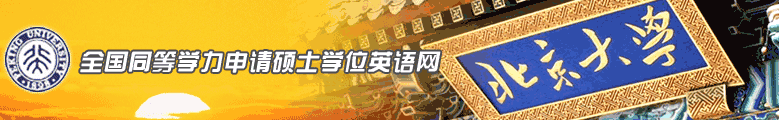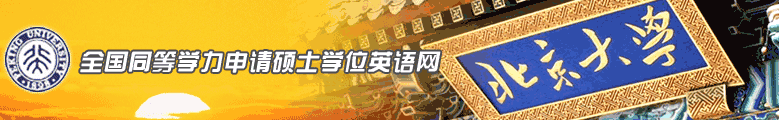|
体悟中的北大精神:朗润园
|
| 日期:2005年5月28日 访问:3877 |
|
|
体悟中的北大精神:朗润园
李鹏宇
朗润园是我求学的地方。
朗润园坐落在未名湖北岸的小岛上,四面环水,古树参天,曾经是满清王府和军机处所在地,至今还存有嘉庆帝亲笔题写的匾额和恭亲王奕忻的墨迹。作为满清圆明园的一部分,古人的亭台楼榭早已在百年前那场大火劫掠中灰飞烟灭了无痕迹,如今的几座四合院建筑皆为后人仿古之作。即便如此,朗润园仍然是北大最美的地方之一。在烈日炎炎的夏日,小岛四周的荷花盛开了,肥绿瘦红将岛上的庭院回廊装点得雍容典雅,韵味十足。到了冬天,皑皑白雪压住红墙碧瓦,淤泥露出干涸的湖水,树枝间鸟雀乱飞,别具一番风味。
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,但面对朗润园,偶尔还是会禁不住想象一百多年前王侯出没的景象。想象他们究竟用何种仪态举止打点国家大事,日出而至日落而归;想象那些悬系帝国命运的奏折如何被讨论、草拟、呈送而出;想象当日的小岛是怎样的门禁森严,神秘莫测。而更多的,我会问自己那些在封尘的彼岸拖着长辫身着官服、口操南腔北调的古人们到底与计算机时代的我们有何不同。也许他们内心深处的思虑盘算与历史这一头的我们并无二致,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,面对同样的是非恩怨荣辱盛衰,做着同样的反应和抉择。毕竟,人性的变迁何其艰难缓慢,从原始人到现代人,经历千百万年,其实仅仅迈出了一小步。历史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,从井口望去,明知另一端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倒影罢了,但却什么也看不见,因为那倒影早已湮没在如烟往事之中,被距离的黑暗紧紧包裹着,像猜不透的谜。
朗润园旁边住着季羡林老先生,八九十岁了吧,岛边山石上“朗润园”三字就是他所题写。但在朗润园学习的三年间我从未见到过他,只是偶尔会在杂志上读到他的一些文章。那是一些冲淡朴素的文字,记录着老人对往事的点滴记忆。对于我们,季老先生这些人就像是古书中的人物,活在一个迥异的时空,通晓一些奇怪的文字,做一辈子世人陌生的学问,冷板凳坐得怡然自得。对于北大,他们是最后一批旧式文人,出生在遥远的年代,经历过中学繁盛,也经历过西学东渐;经历过乱世的中国,也经历过重洋万里的欧美;经历过文以载道的尊容,也经历过师道尊严的毁弃与复苏。如今,他们散落各个院系,安居于燕南、燕北,以及其它地方,在关注或落寞之中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。我试图弄明白这些老先生会用何种心思面对周围的时事变迁,用何种眼光打量我们的一切。但我得不出答案,毕竟这是一个关于两个世代的命题,复杂而艰深。
也许他们并不面对也并不打量,因为他们早习以为常。
|
|
|